自由的火焰在延续:纪念1933与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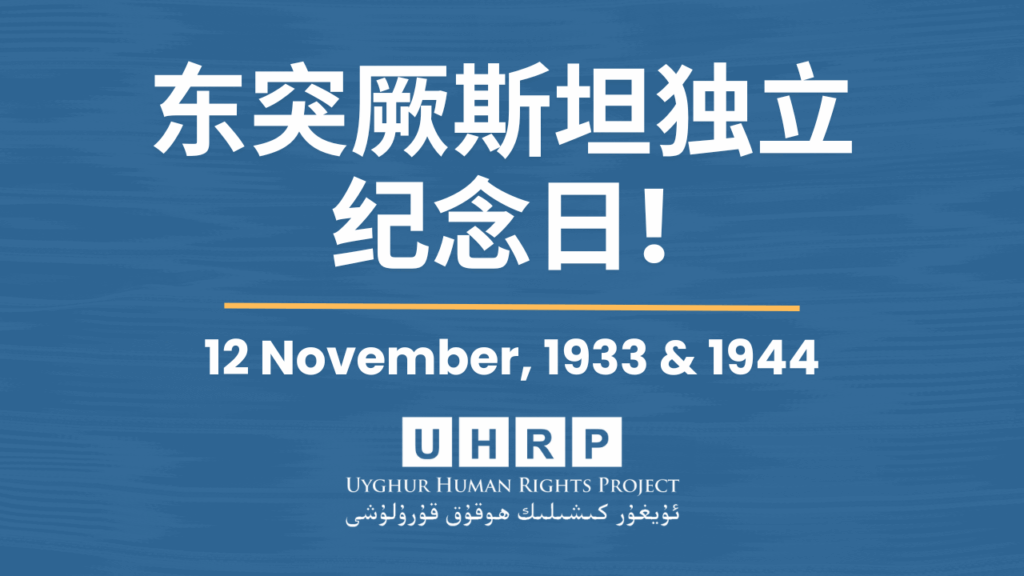
2025年11月11日|阿斯娅(Asiye Uyghur), 特邀作者
十一月十二日,这个日期在维吾尔民族的历史中闪耀着两次独立的光。1933年,第一座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诞生;十一年后,1944年,同样在这一天,第二座共和国再次升起。两次共和国虽都短暂,却在民族命运的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25年的今天,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再次纪念这两段历史,以此重申:自由可以被剥夺,但渴望自由的意志,从未被征服。
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在旧秩序崩塌、民族觉醒高涨的时代中诞生的。那时的中亚与所谓的中华民国动荡不安,帝国主义的重新崛起与地方军阀的争斗让维吾尔人民陷入苦难。清朝末年,随着立宪运动的兴起,出现了“五族大同”①的思想,希望在清朝的统治框架下实现各民族——特别是汉、满、蒙、维(回)、藏——共同组成新中国的理想,追求和谐共处。然而,清朝灭亡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却逐渐走向极端民族主义的方向,把“国家一体化”变成了对非汉民族的同化与压制①。对于维吾尔人来说,这种趋势意味着他们的土地、语言、宗教与民族身份将被彻底吞没。在这种情况下,维吾尔人民别无选择,只能举起自由与独立的旗帜,以坚定的决心抗争,守护属于自己的尊严与未来。虽然第一共和国在外部势力的夹击与内部困难中仅维持数月,但它是维吾尔民族第一次以国家形式表达“自决”的意志。这一短暂的尝试,开启了维吾尔人民现代政治觉醒的篇章,也为后来无数人的信仰与奋斗奠定了精神根基。
国家的宣布不仅是政治边界的划定,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彰显。一国的建立,意味着人民集体对自身历史、文化与未来的重新主张;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想象力在公共领域被唤醒。对当时的维吾尔人而言,共和国的成立既是对过往压迫的答复,也是对未来自主治理可能性的试验——无论结局如何,这一尝试本身就具有深远的象征意义。
十一年后,1944年11月12日,第二座共和国在更为险恶的局势中燃起自由的火焰。它不再只是理想的象征,而是实践的勇气。共和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军队、教育与外交体系,在短短五年间展示了民族自我治理的能力③。这一时期,不只是机构的建构,更是社会生活和文化再造的过程:语言教育、社会服务与社区组织的运作,证明了民族自我管理的可能性。尽管在大国政治的博弈与妥协下,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最终被迫解体,但它留下的治理经验与集体记忆,继续在维吾尔人的政治想象中发酵与延续。
回顾两次共和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主权的实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在长期的抗争、探索与牺牲中逐步累积的。共和国的建立与崩溃,折射出的是一个民族在全球与区域权力格局中追求尊严与自决的复杂道路。历史并非单线的胜利或失败,而是持续的实践与记忆的堆叠。
七十多年过去,历史的轮回似乎从未在这片土地上消失。维吾尔人在中共统治下依然未能摆脱殖民的命运。在中共国极端民族主义的阴影之下,维吾尔人自“土改”至“文革”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迫害。文革结束后,中共国推行所谓的“改革开放”,向西方敞开大门,经济与社会结构迅速转型。然而,这场改革并未给维吾尔人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改变或福祉。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中共中央以“新疆建设兵团比地方更具备先富起来的条件”为由 ④,将兵团与沿海开放城市同等对待,使其享受优先发展的政策和资源。与此同时,维吾尔人却被排除在改革的红利之外,被边缘化、污名化和系统性地贫困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维吾尔人已经成为中共国境内最贫困的群体之一。⑤
讽刺的是,这种贫困的真实原因——政策性的剥夺与结构性的压迫——却被有意掩盖。官方舆论把维吾尔人的贫困归咎于所谓的“宗教极端思想”和“文化落后”,并以此为借口提出“帮助维吾尔人摆脱贫困,走向文明”的口号。然而,正是这种逻辑,使“扶贫”与“去极端化”合二为一,成为新的统治工具。
中共国以“反恐”和“去极端化”的名义,开设集中营、强迫劳动、实施宗教禁令、压制维吾尔语言、摧毁文化遗迹——这些政策不仅摧毁了一个民族的身份与精神,也在法律与行政层面上形成了事实上的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的灵魂在这一过程中被剥离,而世界的沉默则成为压迫者更大的底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纪念与记忆的实践显得尤为重要。它们不仅是民族存在感的维系,更是对自由与尊严的持续呼唤。唯有通过记忆的延续与真相的讲述,维吾尔民族才能在被抹除的历史中重新确认自我存在的意义。
当下的压迫并非仅是政治或法律层面的统治,它亦穿透家庭、语言与教育的日常生活。文化空间被收缩,传统仪式变得隐秘,公共表达受限,甚至历史教化也遭到阻隔。在这样的环境中,纪念日不只是缅怀过去的事件,它成为了集体身份的维系机制——通过讲述、通过仪式、通过教育,一代又一代将那些可能被抹去的记忆重新带回公共领域。
然而,维吾尔人没有放弃。他们在流亡中守护历史,在学术、艺术与人权工作中继续发声。有人用学术记录真相,有人用艺术传递信念,有人用语言守护记忆。他们明白,记忆本身就是抵抗,而讲述是对遗忘的拒绝。每年的共和国纪念日,维吾尔人以升旗、祈祷、讲述历史、诵读诗歌、发表演讲、教育子女等形式,在不同的角落延续民族的精神。这些纪念不仅仅是仪式,更是一种集体的誓言——宣告维吾尔民族依然存在,依然在为自由而奋斗。
对维吾尔人而言,自由不是浪漫的口号,而是生存的意义。它存在于母亲偷偷教孩子说母语的课堂上,存在于学者在流亡中讲述被禁历史的讲座中,存在于流亡者夜深时的祈祷与诗句里。自由,是血脉相传的信念,是即便在黑暗中也不肯低头的意志。也许自由不会立刻到来,但希望从未离开。信念如火种,穿越压迫与时空,在每一个维吾尔人的心中延续。
纪念1933年与1944年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不是为了沉湎过去,而是为了延续精神。这种精神,象征着尊严、勇气与自决,是在历史最黑暗时刻点燃的光。今日的纪念,是对压迫的回击,也是对未来的召唤。我们必须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政治权力的更迭不会自动带来公正,唯有通过持续的社会实践、跨代的教育与国际的声援,民族的权利与记忆才能得以维护与再生。
结语并非简单的慰藉,而是行动与反思的号召。只要心念不灭,维吾尔人就不会消失;只要维吾尔人还在,他们的家园就不会消失;而他们的自由梦,终将成为现实。火焰不灭,自由不息。谨以此文,纪念1933与1944年的两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参考资料 / References:
① 周锡瑞:《清末宪政运动与民族问题》,《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相关学术讨论链接:https://www.lhp.sdu.edu.cn/__local/1/26/0E/2B9E90910BDAF6B8AD5A62C3924_F9487A03_685368.pdf)
② 刘晓原:《从“ 五族共和 ”到五域统合——辛亥革命和中国国家形态近代转型》, 收录论文稿(学术论文PDF)。(下载链接:https://newdoc.nccu.edu.tw/teasyllabus/259007209003/%E4%BA%94%E6%97%8F%E5%85%B1%E5%92%8C%E5%8A%89%E6%9B%89%E5%8E%9F%E8%AB%96%E6%96%87.pdf)
③ Linda Benson, *The Ili Rebellion: The Moslem Challenge to Chinese Authority in Xinjiang, 1944–1949*, M.E. Sharpe, 1990.(Google Books:https://books.google.com/books/about/The_Ili_Rebellion.html?id=suuXIhetjZcC)
④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志编委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WorldCat目录:https://search.worldcat.org/title/303275227)
⑤ 新疆统计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2020)》及历年数据。(年鉴条目:https://www.zgtjnj.org/navibooklist-n3020013096-1.html;新疆统计局主页:https://tjj.xinjiang.gov.cn/)
